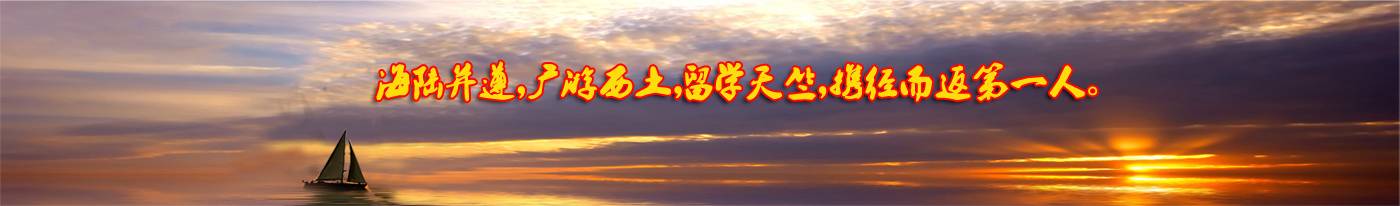
坚韧不拔修大道(作者:郭天印 张剑)
在前面两篇文章中,我们说到了法显大师西天取经的原动力与爱国情。今天,我们将对大师在佛学修为与追求真理道路上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做一些浅涉探讨。
法显西行,始于东晋安帝隆安3年。他的出发点为长安,经河西走廊,穿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达新疆,又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达于阗。略经休整,再次启程,越葱岭,取道印度河流域,经巴基斯坦到达阿富汗,再由阿富汗折返巴基斯坦,历经艰辛,终于进入恒河流域,又横跨尼泊尔南部,最终到达东天竺,并在此留学3年。
漫漫长路,说起来容易,但在1600年前,法显和他的同伴们既无飞机,也无汽车,还没有孙悟空猪八戒那样的徒弟和观音菩萨等诸般神仙的护佑,其艰难险阻如果不是亲历,那是真的想象不出来的。试举一例,越过大沙河,法显在《佛国记》中这样写道:“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这条沙河究竟是指哪一条河?今人尚在辨析,但我们从中可以体悟到的是什么?是恐怖,是毛骨悚然,是前途莫测,是举目无助。也就是说,法显他们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并不是害怕有人,哪怕是强盗,而是苦于无人,甚至连鬼都没有的孤独与无助。他们置身于那个特殊的环境,唯有强大的心力才可以战胜一切。好在,对于横下一条心、这条路一定要走到底的信念坚定者来说,孤独与恐惧又算得了什么?这样的沙河,法显走过去了,紧接着,他们又翻越了终年积雪的的大雪山、断粮缺水的无人区。可以说,面对这样的旅行,超凡的意志、强健的体魄、冷静的判断、团队的互助,四者缺一不可。而作为组织者和实施者,法显在其中的作用可想而知。
法显西行之时,已经六十五岁,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代,这样的年龄,早该隐退江湖,颐养天年去了。而法显却偏偏在这个年龄勇敢地走上了西天取经的道路。既到天竺,法显便沉下心来,苦读钻研。可以说后来留学生们所能碰到的困难,他都碰到了,后人们根本不可能想象的困难,他也遇到了。和任何留学生一样,语言关是必须攻克的。法显在东土的时候对梵文一窍不通,而精读佛经,研究佛学,又岂能靠别人翻译?所以,法显的第一门功课正是学习梵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法显很快就将这门并不好学的语言精学到家,不仅可以流畅地通读佛经圣典,而且可以用这种语言和当地的法师们自如交流。由白丁到大师,这个过程,仅仅3年而已。3年以后,东土圣僧法显就可以在天竺的佛坛上开讲佛经了。这可真是一桩奇迹,前无古人的奇迹。大约又过了两年,法显在天竺佛教界已是名极一时的高僧,而当初与法显同行取经者,有的已经圆寂升天,有的旁出左道,成为在印度和南亚享有盛名的商人大贾。法显征求这些幸存者的意见,竟无一人愿意回归故国。当然其中原因诸多,譬如这些人大部分已经年事颇高等等。法显在对这些老友逐个征求意见之后,毅然决然地以独行者的姿态踏上归途,他要用生命的最后部分来完成毕生之愿。
法显的归途自是别一番风景,也是别一番惊涛骇浪。他由东天竺携大批佛经乘船先到狮子国(斯里兰卡),在这里历经两年,又得到不少稀有经书,然后开始由海路归国的艰险旅程。越印度尼西亚,换船北航,在几次台风中颠簸流离,最终于东晋义熙9年(413年)在青岛登陆,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时,距离法显去国远行已经整整一十四年,而法显已是年届八十的耄耋老人。然而,对法显来说,归国只是完成事业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还将把那上百万字的佛经用生命的最后时光来完成由梵文翻译为汉语的壮举。他别无所靠,只能靠自己来完成,他别无所求,因为他的生命正在于用自己的光焰照亮信徒们前进的道路,以生命的流逝来约束佛家弟子行动的轨迹。
法显,以他的全部心血和能量,翻译了佛经,实现了愿望,也以他全部的生命注释了什么是“坚韧不拔”。
2023.9.28